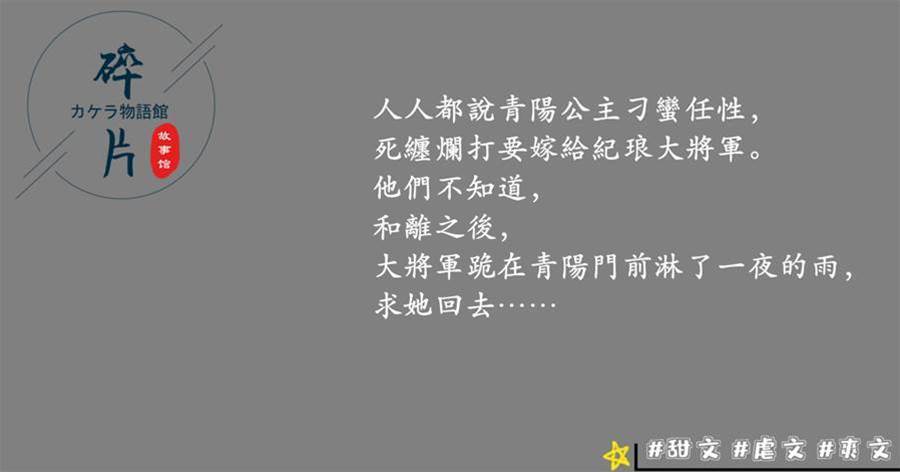《和離後,駙馬悔不當初》第4章
但所謂世,最最怕最最尋常,便『無常』字。
過兩,紀老將軍紀子都戰。
夕之,紀瑯從京都霸王變成紀獨苗。更怕,根獨苗還,非戰。
當皇弟已經登帝位,也敬仰公主。到消息沖到殿候,都沒喘勻就號施令:「許讓紀瑯戰!」
皇帝弟弟笑著著,然問句:「為何?」
因為捨得。捨得讓嘗邊塞苦,捨得歲便擔負起個紀……
但些話,,畢竟還個姑娘,皮得很。
于,擠句言由衷話:「宮裡陪解悶!」
樣,句!
驟然從裡驚,背已經汗涔涔片,吹,凍得都涼。
還清楚記得——句話之,紀瑯從屏,青,似乎受到莫侮辱。
泛著目掃:「公主把當解悶玩,卻更願征戰邊疆,馬革裹屍。」
第反應讓句晦話,然才反應過。
個猶豫,便忘解釋。
直到紀瑯拂袖,才回過神起辯解:「故。」
皇弟為何歎:「皇姐,朕已經允。紀軍能無帶領。」
,紀滿英烈,骨子裡流著武將血。勸紀瑯,只惹而已。
個,著。
紀瑯之,費盡拿到邊疆報,妄圖裡尋得儀隻言片語。
樣苦子持續兩個,握著拼湊點兒微消息沾沾自候,林瑤所措到:「公主,麼辦?」
著拿封暗信封,面好正楷,只瞧見落款,睛就克制——紀子紀瑯。
紀瑯林瑤信。
像個傻子樣努力推敲過得好好候,林瑤封信。
林瑤歎問:「回起,公主,個法子幫斷吧。」
捏著封信,像握滾燙——燙得指尖痛,連也痛。
清楚,紀瑯柔神並屬于,卻還捏得緊緊,沒鬆。
信裡都無比珍。自己況,自己抱負。最句——若嫌麻煩,能否許每寄封信過。京都,願斷。
斟酌字句裡,都翼翼。從沒見過般謹慎微紀瑯。悅之面,都般膽怯吧。
個,捏著封信,盯著燭夜未眠。話本裡剜之痛,終于到。
只,並沒該樣耍段搶回紀瑯,也沒否順推舟紀瑯份。只,該如何回信。
捨得紀瑯難過,捨得像樣,悄悄個卻得到回音。
于,乍破候,磨墨,提起,歪歪扭扭用林瑤吻紀瑯回封信。信裡只因為傷,所以暫用代替。
到兒,舉起,借著透點點,揉揉角。
用紀瑯字,。練漂亮簪楷。
都『見字如面』。著從軍營裡誰都兵成將軍。著成起,驕傲郎。
張子棟婚約被拖再拖,為避張首輔個老匹夫催促,至始裝病。而張子棟就宮候,撞見剛從宮裡林瑤。
沒麼幸運,全然兩相悅什麼樣。
們兩個跪面承認私候,第反應——紀瑯,該傷。
到能失落,眶泛。裡就揪著疼。

 上一章
上一章
 下一章
下一章
 目录
目录
 分享
分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