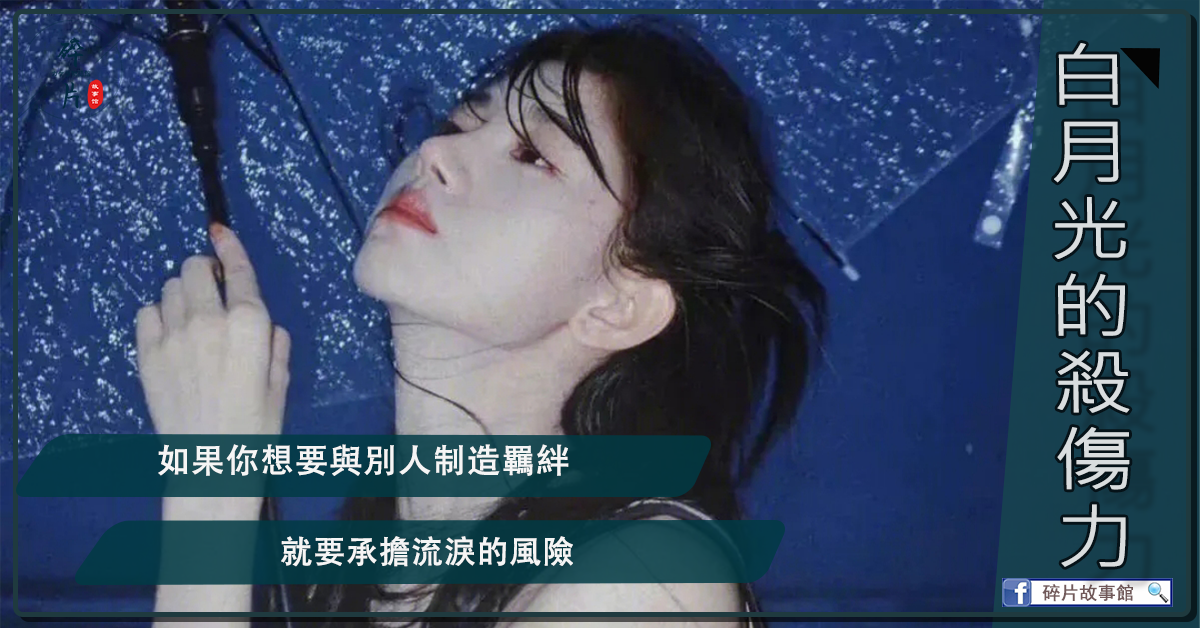《論白月光的殺傷力》第8章
婚禮當天,我過得云里霧里,像只傀儡一樣,終于來到木頭人不熟悉的流程。
幾次磕磕絆絆,莫名走神。
聽著兩人互相應答了儀式,一旁的陳阿姨眼含熱淚,就連鐘昀父母都特別激動,幸福得連說話都結巴了好幾次。
一個個面孔,明明是還算熟悉的人,突然變得那麼陌生。
去洗手間洗了把臉,鏡中的我也分外陌生,看著也并不適合出現在這里。
陳曦幾次用眼神暗示我怎麼了,我回以一個笑容。她不信,卻也忙得湊不過來問兩句。
婚禮臺上,陳曦長長落地的白色婚紗,垂在我腳邊,我們一行不怎麼互相熟絡的伴娘、伴郎站在那兒,看著新娘的捧花,等它花落誰家。
場上的喧囂忽然一靜,陳曦轉過身來,沒有選擇往后拋捧花。
反而走近我,她朝我伸出手,我順勢上了臺。
她手里握著話筒,「葉子,今天是我最幸福的一天,在這個時刻,我想要將這束代表交接幸福的捧花,交給你。」
「我,鐘昀,還有你,我們三個永遠是最好的朋友。」
她笑著,笑得溫柔又耀眼。
就像高中那年,我狂奔去他們兩人高中時,見到的那一幕。
他們宛若璧人,笑容艷麗,手指相扣。
我站在一旁,多余的觀望,難堪想哭,甚至有些迷茫得不知去路。
曾經留在我記憶中的那些「未來」,至此,被我親手一點點改變、抹去了。
那些情愫、愛慕、溫暖,一切情緒,真正變成了只有我一人知曉的過去。
18
宴上被灌了點酒,我其實是打心底替他們開心的。
可又有某種難過催著我放縱,喝得上了頭,這會兒有點犯暈。
那些壓抑在心底的情緒終于爆發,我眼含淚水,拽住陳曦的手腕問:「我……當時那麼覬覦鐘昀,我那麼卑鄙無恥,那麼古怪孤僻,你為什麼還愿意那麼溫柔地對我?甚至把我當成最好的朋友?」
陳曦十分認真地思索了下,轉過身來和我面對面坐著,一臉嚴肅地反駁我:「葉子,不是的。我給你的遠遠沒你給我的多。如果不是你,我現在甚至不能站在這里。你不僅一點都不卑鄙,你超級好的。不然我哪怕想報恩,也不至于裝到現在嘛!」
她溫熱的手,輕輕替我抹去眼淚,聲音柔而低緩,繼續認真說著:「還有啊,有人流眼淚,會受傷這種事情發生在身邊,我也會很擔心的。就像你不忍心把我丟在那個巷口,遭受折磨一樣。我也不忍心冷眼旁觀你掉眼淚,莫名其妙地就接近你啦。」
她停頓了會兒,說這話的表情有些扭捏和羞澀,但還是微燙著臉開口:「而且呢,我認為,愛不能是始終飽受折磨,冷如死海的。愛是為了活著而存在的。」
「當我們有了自己的愛,也就更容易分辨什麼才是真正的愛啦!葉子你呢,很棒的!你憑借自己擁有了很好的愛,我們也是因為你的人格魅力,而心甘情愿留在你身邊的,才不是什麼單方面施舍呢!葉子,不要哭,你現在真的超厲害——是為自己、為愛自己而活的。」
是的。在她——在朋友的擁抱里,我泣不成聲。
為愛而生,為己而活。
在擁有專屬自己的溫柔月光之前,先努力地照亮自己吧。我如是想著。
腦海中忽然閃過陳曦小時候的臉——我想起來了,小學時拯救我于校園霸凌中的女同學的名字,她的名字也叫陳曦,只不過后來轉學去了 A 城,她和記憶中長得還是一樣漂亮。
一樣的好。
19
陳曦說完那些話,也不爭氣地哭了。
她不是個多愁善感的人,大概最近恰好是母親生病,這些生離死別、情感最惹人軟化。
后來她也有點微醺了,抱著鐘昀的胳膊,不撒手,邊傻笑邊說:「葉子!幸福不能光靠捧花,我最近發現不少帥男人,你等我一個一個給你打包送來!」
鐘昀噗嗤一聲沒忍住,他笑得無奈,抬眼看向還未收場的宴席。
葉落百無聊賴地雙手搭著下巴,表情放空不知道在想什麼,時不時抬起手背擦擦眼淚,盡管眼里沒有淚。
她喃喃自語:「草,看到他們結婚,我忽然也好想談戀愛。」后面又像是罵了某個人是大傻戳,看唇形像是倆字兒的名。
鐘昀打了個哈欠,低下眉眼,順了順陳曦的發頂,很溫柔地講:「誒,到時候可以問問葉子需不需要。但其實吧……」
鐘昀看向在場上另一個大學男同學,那屆高嶺之花,半邊校友戲稱校草。
聽說他似乎早就有了暗戀的女生,到現在也堅持如一。那人眼里,滿滿都是那個正發呆的姑娘。
而那個被暗戀的、充當白月光的女孩子是誰,也就可想而知了。
鐘昀笑了,他心想:「你在窗內看月光,看月光的人自窗外看你。」
他隔著老遠的距離,莫名其妙地想和那姑娘說句話——
「你也會有的。屬于自己的溫柔月光。」

 上一章
上一章
 下一章
下一章
 目录
目录
 分享
分享